评论对象: 未来 | 2006/3/27 10:32:54
评论言论:
康素罗的故事
文:[法]阿兰·维尔贡德莱
译:马振骋
哥伦比亚作家齐尔曼·亚西梅加斯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每个人谈论康素罗,就像谈论把火焰喷到了巴黎屋顶上的萨尔瓦多小火山。凡是有关她的第一个丈夫恩里克·高曼·加里略,她的第二个丈夫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轶事,没一次不提到她。她嫁给高曼加里略以后,做了梅特林克、莫莱亚斯、邓南遮的密友。她1927年守寡,1931年再嫁给圣埃克苏佩里,她那时的朋友有纪德、莫洛亚、德·鲁杰蒙、布勒东、毕加索、达利、米罗……他们生活的圈子里有飞行员和作家。当圣埃克苏佩里正在创作至今还风靡全球的《小王子》时,莫洛亚曾去他家做客。用过晚餐,开始玩纸牌、下象棋。然后主人要大家都上床睡觉,因为他想工作了。几小时后,莫洛亚听到楼梯口的喊叫声:“康素罗!康素罗!”他慌慌张张出来,以为房子着火了,其实不过是圣埃克苏佩里肚子饿了,要妻子给他煮鸡蛋……”
“如果康素罗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把他们夫妻生活中的这些插曲,生动滑稽地写出来,大家会确信她是丈夫作家的缪斯。她是画家、雕塑家,文笔流畅,很有才气,但是她的往事……她只说不写。”
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1930年初次遇到圣埃克苏佩里,15年后,康素罗在美国过着孤独的流亡生活,这时她叙述作家兼飞行员与她的生活,用松散倾斜的字迹盖满整页纸,经常涂改得难以辨认。然后细心地打在薄纸上,笨拙地装订成册,放进一只黑色硬纸盒里。
《玫瑰的回忆》——“岛国小鸟”的最后一段趣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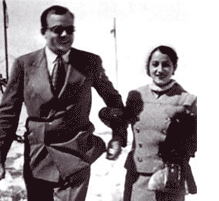 时间是1946年。康素罗思念法国,但又害怕回去,尤其担心卷入遗产纠纷,向往到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地方过日子,为此想起了马略尔卡岛的帕尔马,她说,“为了纪念乔治·桑和缪塞”——另外两个“可怕的孩子”。
时间是1946年。康素罗思念法国,但又害怕回去,尤其担心卷入遗产纠纷,向往到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地方过日子,为此想起了马略尔卡岛的帕尔马,她说,“为了纪念乔治·桑和缪塞”——另外两个“可怕的孩子”。
自从1944年7月丈夫失踪以后,康素罗在纽约深居简出,给商店橱窗设计布置,做模型,生活在“东尼奥”的回忆中,面对空穴的葬礼无法释怀,双重的失落椎心泣血。她撰写一些有头无尾的小文章,对着录音机回忆往事,把完成的章节用打字机打出来,但是中美洲人的豪放禀性使她不能自制,还用另一种方式把东尼奥的面目“写”在石头和黏土上。她也用铅笔、炭墨、水彩来画画。她想回到富叶园,那是1940年圣埃克苏佩里出国前租赁、现已无人居住的大庄园。她说愿意回到那里去“找回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你的肖像”。
在失去的人与她之间展开了对话。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在欧洲,圣埃克苏佩里的失踪为传奇打下了根基。大家给他树碑,大家把他神化,他成了天使、神品天使、蜡翼融化坠海而死的伊卡洛斯、没有回到自己星球的小王子;天空的英雄,在宇宙中粉身碎骨。至于康素罗,不大有人谈起,影踪不见,甚至遭到否认;好在编造的神话中缺了她也行;虽则她掌握了许多钥匙。在背景中也不期望有她出场,毕竟在圣埃克苏佩里的英雄贵族故事中她太刺眼了。圣埃克苏佩里的传记作者很少知道她的生活,只是歪曲她,漠视她,把她看做傻乎乎的怪女人,她婆家的亲朋好友(除了婆婆玛丽)欺侮她,说什么“电影里的伯爵夫人”,“疯疯颠颠、爱使性子的小女人”,“说话唠叨、法语讲得不好”,这使她留下了这样的形象:一个“没有灵魂、不忠诚、卖弄风情的女人”。总之一句话,据人说,她在神话中会令人败兴。
1944一1945年,康素罗——又是据说——“意志消沉”。长久以来,她好歹学会了等待的艺术,自从与圣埃克苏佩里结婚以来,她做的就是这件事:等待。最严酷的等待,可能是1943年3月他出征后几小时的那次。“全世界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起也拗不过您的愿望,我很了解我的丈夫。我一开始就知道的,”在尚未发表的她与他之间的一次虚构对话中她这样说,“是的,我早知道您要走。”她接着又说:“您念念不忘洗刷自己,您就是要在枪林弹雨中洗刷自己。”
1944—1945年:总结的时代,回顾的时代,表面上沸腾、落拓不羁、“艺术家”的生活,就像我们想象中的30年代的艺术界。也是“无愧于”东尼奥活下去的时代。她必须另外找一套公寓,保证得到,即使是菲薄的收入,第三次扮演寡妇的角色。这总算是不再流眼泪的时代了。“我的爱,我已经流干了,”她叫道。怎样节哀呢?“您是永恒的,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把您带在身上,我们像小王子,谁都接触不到。像在光明中谁都接触不到。”康素罗没有多少能耐维护非常难处理的家庭利益和版权利益。她从小就保持了这种有点天真、轻信别人的随意态度,她不了解欧洲人狡猾的办事方法,对钩心斗角不感兴趣……况且,她跟圣埃克苏佩里过的是不受社会规则约束的生活,这种生活加上天性,更使她做事过分、多愁善感、马马虎虎。她一直是怎么想就怎么过,也就继续这样想这样过:她凭本性往前进,重建生活。
她的豪情和活动完全来自她在萨尔瓦多度过的童年,1901年她生在那个国家。童年本来充满奇思异想,中美洲人的想象力更把童年美化了;她生来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娓娓动听,绘声绘色,现实经她一打扮变成了故事,叫人听了入迷。她懂得如何渲染一件真实的事,编导自己的身世,萨尔瓦多带着它的焦土、火山和地震成为一个传奇国家。她是这么一个国家的精灵和仙子。在平静幸福的日子里,圣埃克苏佩里总是叫她讲萨尔瓦多的故事,那时她还是个孩子,在父亲的咖啡种植园里跟印第安人玩,四周是香蕉树。“给我讲蜜蜂的故事,”他要求她,犹如小王子要求“给我画……”,康素罗讲了起来。圣埃克苏佩里对她说:“当我在星星中间,当我看见远处一团火光,我不知道这是一颗星,还是地球上一盏在给我打信号的灯,我对自己说这是我的小康素罗,她要我回去,讲故事给我听,我向你保证我会朝着这团火光飞过来的。”
这段童年,康素罗把它带在身上,在最艰难的岁月:圣埃克苏佩里的不忠、归期不定的离别、飞机失事、最后的失踪,也是这段童年救了她。她也可以这么说:“我来自我的童年。”
她的暴躁、极端和巴洛克式的天性——在她那片大陆上,讲故事的大家如博尔赫斯、科埃萨尔、马尔克斯无不如此——对圣埃克苏佩里倒是一种幸运。她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怪癖、落拓不羁的天性,诗意地过日子:他们两人都有这种精神贵族的独立性,这种超现实主义的禀赋,把尘世生活过得像传奇,像寓言。
在圣埃克苏佩里死后养成的这种想象力和生命力,才使康素罗不至于伤恸欲绝。她于是写她的回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相遇,一波三折的订婚仪式,给家里人介绍,结婚仪式,定居巴黎,媳妇生活,圣埃克苏佩里的生存困难,他的外遇,他的感人的唐璜作风,找回昔日的温情,搬家,其他女人,徬徨生活,飞行事故,书籍出版和成名;出走,在沃克吕兹省奥佩特的集体生活,前往纽约,白色大房子,异乡客地的孤独,她的东尼奥的出征告别,平静灰色的赫德森河水,河面下潜艇悄悄行驶,带着他走上了不归路……
她写回忆一气呵成,带着她做事一贯的奔放洒脱。她在书中冲动而又多情,天真而又顺从,愤慨而又坚定,忠诚而又不忠诚,顽抗而又沮丧。她写文章如同她平时说话,如同她临终前还是这样说话,在磁带上回顾这些往事,忠实地留下了她的声音。这是讲故事人的声音,音调与语式都像她在纽约的好友萨尔瓦多·达利。她说:“关于我的丈夫跟我在家里的私人生活,我很难于启齿。我相信一个女人不应该提这类事,但是我去世前又不得不提,因为人家对我们的家庭生活说的不是实话,我不愿意让这种事继续下去。我还是勉为其难,去回顾这些每个婚姻中都会遇到的困难时刻。说实在的,当神父说你们是为了生死共命而结合的,这话很对!”
1946—1979年。她与圣埃克苏佩里过的一生,信函与资料,作家画的素描,水彩画,蓝笔肖像,《小王子》一书的素描,老影剧节目单,涂上小人像的菜单,电报,地图,明信片,草稿本,没有发表的诗和文章,数学研究专利和笔记本,一辈子的全部宝藏统统放进了几只甘于寂寞的机舱箱子。装在运输机的货舱里横渡大西洋。搬进康素罗在巴黎的公寓的地下室,此后没有完全打开过,任其像古档案似的神秘莫测。
有时,在暮年,她回首往事,大胆去探索埋在黑夜里的箱子。“我打开卷宗和箱子,”她说,“没有一次不发抖,里面堆着丈夫的书信、图画、电报……这些发黄的纸页,零零星星画着高杆儿的花和小王子,是这个失去的幸福的见证,我一年比一年深切地感到我享受的圣恩和特权。”
回法国后的那几年,她住在巴黎和格拉斯。她的雕塑与绘画事业也趋于稳定。她花许多时间支持圣埃克苏佩里的纪念活动。她作为德·圣埃克苏佩里伯爵夫人,为国捐躯的大作家的遗孀,参加纪念会、开幕式、庆祝会;她这样做,是看做一项责任,不一定符合自己的意趣。她从来不喜欢学院仪式、社交、情面难却的邀请。她宁愿回忆她在1944年6月底他逝世前夕写给他的东西:“你在我心中犹如植物在地里。我爱你,你,我的宝贝,你我的世界。”还有他给她的回信:两个人像森林中的两棵树纠结不分离,那有多么舒坦啊。被同样的大风摇撼,一起接受阳光、月光和夜鸟。一生一世。
1979年康素罗逝世,权利所有人继承了那一堆箱子和资料。箱子始终没有打开。搬到了格拉斯的农舍又沉睡了几年。慢慢地,继承人把它们挖掘了出来,重见天日。1999年,为了纪念圣埃克苏佩里诞生100周年,这些资料交给了我们,供我们研究。这样《玫瑰的回忆》,由康素罗费心在美国制成缩微胶卷的夫妻两地通讯,《小王子》的草稿,才复活了……
康素罗又有了生命。那个被大家掩藏了那么久的人又出现了,可以说还了她一身清白。
通过这个从未有人过目的私下对话,整个故事突然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热情,冲动,复杂。康素罗与圣埃克苏佩里的关系是了解作家的基础。没有康素罗,他会真的是圣埃克苏佩里吗?这些资料的披露使他回复原有的人性。要说他的神话会剥落开裂,他的肖像也不完全像大家为了千古流传而画的那样,好比在涂香料的面孔上加了一层精致的蜡,就是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
很少传记作家好好了解过这对夫妻的历史以及夫妻情谊对圣埃克苏佩里的影响,因为缺少必要的钥匙。没有人曾经深入地窥测这种关系中他人难以识破的奥秘。要从这个角度去阅读《玫瑰的回忆》。阅读这部写事迹的书。首先是写等待的书。
因为往事的叙述是以等待开始,也是以等待结束的。全书从头到尾是这么一个人的历史,他出现又不见了,他溜走又归来了,他逃避又返回了,他寻找自我又失去了自我。问题的中心是爱,尤其是被爱。还提到了监护他的母亲,当家人,使童年充满欢乐的妈妈,忠贞与终生为伴的象征。这些主题的理想化,转而对女人的钟情。不是一切女人,其中有理想的女人,也有“候客室”,“小母鸡”,什么嘉比、蓓蒂,“小虎皮鹦鹉”,这都是康素罗给她们起的绰号。
圣埃克苏佩里心中深深铭记着理想女人的形象:关心家务,人间仙女,基督信女的原型人物,“神的侍女”。康素罗决不是外界传说的那个轻浮或颠三倒四的女人,她从父母那里接受了颇为严格的教育,她的母亲据她自己说对她很严厉,用基督教义和民间信仰培养她。她嫁给了圣埃克苏佩里,是不是就要做他自己也说不清的贤妻了呢?她在回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认真扮演自己的角色,整理他的衣服,准备他的行装,操心让他吃得好,布置和打扫他的书房,尤其她等待。康素罗对这个角色认真学习了很久。异国性情的浮躁,有时就忽视了常规;康素罗要说话,不知道保持圣埃克苏佩里为了写作与思考需要的安静,她还是要说,也就说得不是时候了。
这就够他往外走了。他轻易地受到有些倾向的影响,让恶意的人有隙可乘,被女崇拜者花言巧语迷惑。他爱的——他也说得一清二楚一一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过日子,做他想做的事,不要欠别人的情,但是要自由。他的独立欲望又跟心中根深蒂固的眷恋感情相冲突。于是对着康素罗经过升华的印象屡屡哀求:康素罗,像朵盛开的花等着我回来……康素罗,天赐的小光明……我的小鸡……把房子收拾干净……,给我做一件爱情斗篷……康素罗,我的甜蜜的义务……
圣埃克苏佩里不同凡俗的生存境遇,迫使他在感情上长年彷徨,只有在孤独和黑夜的飞行中,在缠绵心头为国战斗的欲望中才得到宣泄和解放。面对死亡的大无畏挑战,不惜牺牲的殊死抗争,给他弥补了感情上的失落。行动,情谊,正直,发展到英雄主义的爱国主义,看做是升华形态与二度净洁手段的飞行,都成了一个个中途站和桥梁,帮助他挣脱他所陷入的感情牢笼。康素罗的这部回忆非常清楚地解释了这份悱恻动人的追求。
他们的生活只是一系列离别与重逢,背景则是偶然性很强的飞行,变换地址,意外事故,危机,争吵,沉默,突然出走和在淳朴的富叶园里短暂的田园生活,康素罗要保持那里的莫奈式情调。然而,这样的爱情是不会真正毁灭的。康素罗疲惫痛苦,异国风情则依然不减,最终接受了其他人的致意,建筑师贝尔纳·赫富斯见了她爱得发狂,德尼·德·鲁杰蒙在纽约住在他们附近,对康素罗殷勤有礼,在她的丈夫失踪后,给了她不少安慰。他们那种古典悲剧式的恋情只能在这种紧张状态、这种离别中才能生存一一这事反而一天比一天更让人坚信:这是拆不散的一对,那时圣埃克苏佩里向她承认了是她战胜了所有的其他女人。他还对她说她是他的安慰、他的星星、他家的灯光。身处两难、受人冷落、又被催着回来的康素罗,对他才是不可缺失的。尽管他有情妇,有贵人名媛送他礼物,保证他的作家事业,奉承他,有时还真心地爱他,康素罗依然是不可根除的。然而她还是免不了受批评和轻视。她是家庭里的外国人,在《新法兰西评论》文学晚会上非常惹眼。纪德讨厌她,但是她说他喜欢的就只是小伙子和老太婆。从她的绘画、素描、照片来看,她自有一种青春朝气,一种超现实主义女性的自由自在,但正是这种靓丽鲜明给她带来了伤害,因为圣埃克苏佩里常去的几家沙龙,女性的个性更解放,知识更丰富,行为更潇洒,还有就是职业女性。康素罗,像圣埃克苏佩里责怪她的,“却只会显示她的宗教虔诚”,祈求上帝和一切圣徒,跑教堂,按时做忏悔,当丈夫出差时为他祷告……然而这又是圣埃克苏佩里复杂性格的另一面,他对宗教迷信表示出一种明显的轻视,却又在皮夹里放一张利雪的圣戴莱莎的宗教像,他1940年回来要求妻子到卢尔德去进香,在圣水池里一起行洗礼!
这些内心矛盾在暗中作梗,使圣埃克苏佩里既颓丧又痛苦,在康素罗的书里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这说明为什么康素罗总是得到召唤,去紧急救援,说到头来她是个他可以信赖的人,是个会收留他的人。唯有她不为他渴慕荣华与名声;她只希望住在非洲小角落的一幢小房子里,让他平静生活,安心写作。因为只有她自始至终要求他写作,避开黑夜的一切诱惑,甚至还把他关到她精心布置的书房里,不写完文章不许出来。
圣埃克苏佩里为此感激她,悄声告诉她多少次梦想在她的羽翼下,在她温婉小鸟般的柔情保护下写作……“您的鸟的语言,可爱的颤抖……”在美国那幢像凡尔赛宫的白色大房子里,他完成了他的杰作《小王子》。那是一段快乐的日子,画画,要朋友摆姿势,重写亲身经历的故事,重新创作组成故事经纬的一切主题。《小王子》是在康素罗的火焰中诞生的,他终于承认……玫瑰确实处于童话的中心。依然是康素罗启发他写出玫瑰的情节,引起他的愧悔,对他的玫瑰竟那么不公正和负情:“但我年纪太小,不懂得爱她。”在“小王子之家”他已经知道,在科西嘉岛他更明白,一切嫌隙都已化为乌有,康素罗原谅了他,小康素罗的重大忧虑已经消除。“告诉我,小康素罗,我的忧虑也消除了吗?”他想到把题词献给她,然而康素罗更愿意题词献给叶翁·维尔特,他的犹太朋友。圣埃克苏佩里现在有点后悔了吧。他答应战后回来写续篇,那时她会是梦中的公主,不再是一朵带刺的玫瑰,他就把那部书献给她。《玫瑰的回忆》,以及尚未出版的书信,证实了这份不同凡俗的爱情。尤其证实了被过于完美的传奇和穿凿附会埋没了的东西:圣埃克苏佩里事实上需要这份被遗忘五十年的手稿,以另一副面貌在人间再生,显得更像个凡人。这份回忆录使他更接近我们。他一下子变得更动人,没那么一本正经,更真实,更亲切。44岁生日那天,离他的死亡只有几个星期,他嘱咐她,给我写信,给我写信,“(邮件)时时刻刻到来,使我心里春意盎然”。
“小康素罗”确实收到了那封信,那条指令。
她写了,她写,叙述他们的故事,让大家听到真相。
2000年2月巴黎
( 选自《译文》2002年第一辑圣埃克絮佩里专题 )


